
州吁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石厚,石厚献策说:“周初分封诸侯有五个等级,即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异姓国家,现在只有宋国(子姓,初封为殷商后裔微子启,都邑在今河南商丘)称公爵为大;同姓国家中,只有鲁国(姬姓,初封为成王叔父周公姬旦,都邑在今山东曲阜) 称叔父为尊。主公如果想讨伐郑国,就必须派使者到这两个国家去游说,求其出兵帮助,并和陈国(妫姓,在今河南淮阳县)、蔡国(姬姓,在今河南上蔡县)的军队结成统一战线,五国共同伐郑,何愁不胜?”
州吁想了想说:“陈、蔡都是小国,历来顺从周王。如今郑国和周王之间产生了隔阂,陈、蔡肯定早已听说了,让他们帮助攻郑国,不愁不来。宋、鲁都是大国,我们怎能指使得动他们呢?只怕他们不会出兵帮助我们吧!”
石厚听了,笑笑说道:“主公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昔日宋宣公传位于他的弟弟宋穆公,宋穆公死前,想报答哥哥的传位之恩,没有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公子冯,而是传给他哥哥的儿子与夷,即宋殇公。宋殇公心地狭窄,公子冯怕被杀害就出奔到了郑国,想借用郑国的力量夺回君位,这一直是宋殇公的一块心病。我们约宋伐郑,这岂不正中其心怀?至于鲁国,鲁隐公只是代理国君,太子轨因年龄小尙未正位。正因为此,鲁隐公执政名不正,言不顺,军政大权实际上操纵在公子翚(hui)的手里。此人贪财好利,只要主公能贿赂以重金,他肯定会出兵助阵。”

州吁听了大喜,立即派遣使者前往鲁、陈、蔡三国,唯有使宋人员难挑,石厚举荐宁翊,说:“此人博古通今,口才伶俐,一定能完成任务。”
州吁就派宁翊使宋。宁翊来到宋国,宋殇公问:“贵国为何要讨伐郑国呢?”
宁翊回答:“郑伯无道,杀弟囚母,公孙滑逃命到我们卫国,他又不念伯侄之情,率师前来讨伐,先君惧怕郑国强大,只好忍辱谢罪。现在我国新君即位,想洗雪耻辱。卫、宋两国同仇共恨,所以,特派我前来借兵。”
宋殇公不解,问:“宋国和郑国并无隔阂,同仇共恨从何谈起呢?”
宁翊环顾左右说:“请屏退侍从,我想单独和您谈谈。”宋殇公让侍从全部退下,然后问:“你有什么话,只管说吧!”宁翊反问道:“您的国君之位是谁传给您的?”“叔父穆公传位于我。”“穆公无子吗?”“有子名冯。”
“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,穆公虽有尧、舜之心,怎奈公子冯却无人臣之意。穆公传位给您,公子冯为何不甘心在宋辅政呢?分明是对失去君位怀恨在心嘛!现在公子冯虽身在异国,但心里却始终可没有忘记重返宋国啊!郑国接纳了公子冯,他们交情已深,一旦郑庄公拥冯兴师向您问罪,宋国人民又感念穆公之恩,因而怀念他的儿子,内外生变,难道您的君位没有失掉的危险吗?所以,我这次前来借兵,名为伐郑,实际上是替您消除隐患啊!如果君侯能出面主事,卫国愿意马前鞍后效劳,若能灭掉郑国,宋则除去了隐患,卫则洗雪了耻辱,岂不是两全其美!”

宋殇公听了这些言语,果然心动,说:“何不约鲁、陈、蔡一同举事?”
宁翊告诉他:“我国国君已分别派遣使者去了。”
宋殇公听了大喜,于是答应亲自率领宋军伐郑。太宰华父督与公子冯关系密切,不愿意宋殇公伐郑,劝阻道:“卫国使臣的话听不得。如果郑伯杀弟囚母有罪,州吁弑兄篡位能说无罪吗?望主公三思而后行。”
宋殇公听不进华文督的劝告,命大司马孔父嘉为将护驾,自领中军出发。
鲁国公子翚接受了州吁的贿赂,便不由隐公作主,自率大军前来会师。陈、蔡的军队也如期到达。宋殇公爵位最高,被推为盟主,卫国石厚为先锋,州吁自领一支军队殿后,五国共有战车一千三百乘,将士十万之众,来到郑国东门外扎下营寨。
大兵压境,郑庄公召来群臣商议,有人主战,有人主和,意见不一。
郑庄公笑了笑说:“你们的意见都不是上策。州叶篡权新立,未得民心,所以借故一些旧的恩怨兴兵来伐,其目的不过是想立威以服众;鲁国公子翚贪图贿赂,事不由君;陈、蔡都与郑无仇,也没有必战的意思;只有宋殇公是真心伐郑,但醉翁之意不在酒,其目标是公子冯,并不是寡人。我把公子冯暂时送到长葛去居住,宋殇公必移师长葛。然后再让公子吕引兵与卫国交锋,只许败,不许胜,白送给州吁一个胜仗,州吁赢得胜利之名,就会得到满足,他国内尚未安定,那敢在此久留?我听说卫国大夫石碏忠心耿耿,他对州吁篡逆大为不满,卫国不久就会发生政变。州吁自顾无暇,哪还有心加害于我?你们看吧,州吁一定会见好就收,马上下令撤兵回国。卫、宋已走,鲁、陈、蔡恋在这里干什么?所以,别看现在大兵压境,其实有惊无
险。”

众大臣对庄公的一番话将信将疑,郑庄公命瑕叔盈率一支军队护送公子冯去长葛。然后又派人给宋殇公送去一封信,信上说:“公子冯逃到我们郑国,因是贵国穆公后裔,我不忍心加害于他。现在,我让他到长葛去伏罪,宋公可以自己去处理此事。”
宋殇公见信,果然不告而别,率领自己的人马包围长葛去了。鲁、陈、蔡三国见宋兵移动,也都产生了撤兵的念头。正在此时,忽报公子吕率郑军从城中杀出,鲁、陈、蔡都不愿意向前,只在原地袖手旁观。石厚只好引兵与公子吕交锋,战没几个回合,公子吕败下阵来,倒拖方天画戟而走。石厚追到城下,守城士卒早已放下吊桥将公子吕接入城中。石厚打了胜仗,命令士兵将新郑城外庄稼收割殆尽,用来犒劳各国将士,然后下令撤兵。众将士不知石厚意图,齐来秉告州吁说:“我们的军队锐气方盛,正好乘胜追击,怎么先锋官却要下令班师?”
州吁一时也弄不明白,派人召来石厚询问。石厚说:“请主公屏退左右,臣有密事启奏。
州吁命身边人都退去。石厚说:“郑国国富民强,郑伯又是当朝卿士,现在被我军打败,这便足够建立主公的威信。主公新立,国事不稳,我担心国内出事,如果在此长久滞留,有了内乱又如何应付?”州吁醒悟,说:“多亏爱卿提醒,都怪我考虑不周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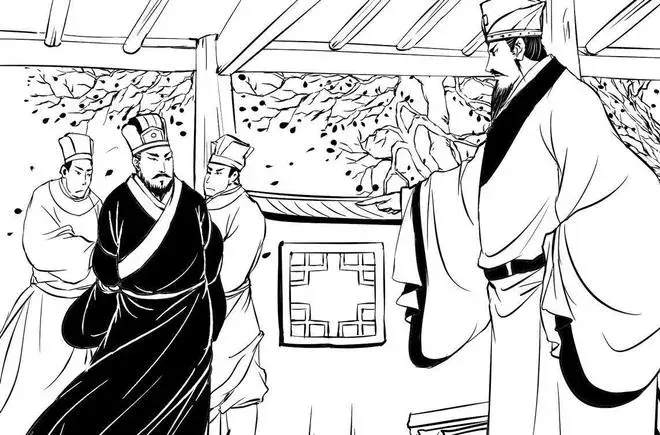
正说着,鲁、陈、蔡三国主帅都来祝贺胜利,也都要趁机班师。 这正合州吁、石厚心意,于是尽班师而去,这次战役总共围困郑国东门五天而已,历史上就叫“东门之役”。
班师路上,石厚自恃有功,命令三军将士沿途高奏凯歌,给州吁壮行。州吁气宇轩昂地回到本国,哪知听到路边看热闹的人却唱出一首不中听的歌谣,歌词是:
一雄毙,
一雄兴,
歌舞变刀兵。
何时见太平?
恨无人兮诉洛京!
州吁听了,很不高兴,他问石厚:“我们已经打了胜仗,怎么还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呢?”
石厚回答:“臣父石碏为前朝上卿,国人都信服他,主公若能将他召人朝中辅政,便会国泰民安。”

州吁回到都城,派人持白璧一双,稻米五百钟,去请石碏人朝议事。哪知石碏借口疾病在身,坚辞不受。
州吁又向石厚:“你父亲不肯入朝,寡人屈身到府上去问计合适吗?”
石厚怕父亲闭门不见,让州吁下不来台,就说:“我代替主公跑一趟吧!”
石厚回到家中,对父亲说:“新君主对您十分敬重,让我来替他召你入朝。”
“召我干什么?”
“只为国中人心不稳,害怕君位不能巩固,想求父亲献一良策。”“诸侯即位,都要先派大臣到周天子那里去请求‘册命’,有了周王的‘册命’和赏赐的冕冠车服,国人自然就信服了,何愁国事不稳?”
石厚听了很高兴,说:“父亲的主意很好,只是无缘无故去朝拜周王,周王肯定会起疑心,如果有人能先在周王那里帮助疏通一下就好办了,请父亲说说,派谁去最合适。”

石碏假装想来想去,过了一会儿说:“陈桓公忠顺周王,朝拜殷勤,很得周王欢心。卫国和陈国一向和睦,最近又有借兵相助之谊,若新主能亲自前往朝拜,央求他在周王面前美言一番,然后入周去请册命’,肯定能成功。”
石厚回到宫中,将父亲的话对州吁复述一遍,州吁喜不自禁,紧命人备了一份厚礼,命石厚护驾,便要亲自去朝拜陈侯。石厚刚走,石碏咬破食指,写一血书,要陈桓公务必帮卫国除害,将州吁、石厚杀掉。
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,陈侯派公子佗出城迎接,先安置在客馆里,公子佗告诉他俩:“陈侯已经做好了准备,明天在太庙里会见你们君臣二位。”州吁见陈侯招待殷勤,心中不胜高兴。
第二天,石厚先到,见太庙门口竖着一板白色木牌,上写"为臣不忠,为子不孝者,不许进入太庙”,石厚问公子佗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这是我国先君的一句遗训,我们国君不敢忘记,立此以教子孙。”
石厚不再怀疑,接着州吁也赶来了。二人走进太庙。公子佗先紧走几步,来到陈侯身边站定,然后大喝一声:“奉周天子之命,只拿下弑君奸贼州吁、石厚二人,其余俱免!”

石厚闻言,还想拔剑搏斗。此时,埋伏在太庙里的武士一拥而上,早将二人擒住,哪里还能动弹?然后,公子佗又宣读了石碏的血书,大家才知道州吁和石厚被擒,原来是石碏的主谋。
陈侯与石碏交情深厚,他知道石厚是石碏的亲生儿子,不忍心杀他,派人到卫国去请示石碏。卫国文武大臣也都说:“篡逆弑君,州吁是首恶,石厚是协从,应当只杀州吁,石厚可以从轻处理。”
石碏不许,说:“州吁之恶,都由逆子酿成,你们替他求情,莫非怀疑我有舐犊私心吗?”
于是,石碏要亲自到卫国去监斩石厚,却被家臣糯羊肩劝住。最后,由猛羊肩代替主子去监斩了石厚。石碏为了安定国家,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,当时人们称赞石碏这一举动是大义灭亲,“大义灭亲”这一成语就是出自这个故事。
卫国除掉州吁之后,从邢国(今河北邢台)迎回了公子晋当了国君,史称卫宣公。卫宣公以石碏为国老,从此陈、卫两国更加郁睦亲善。


